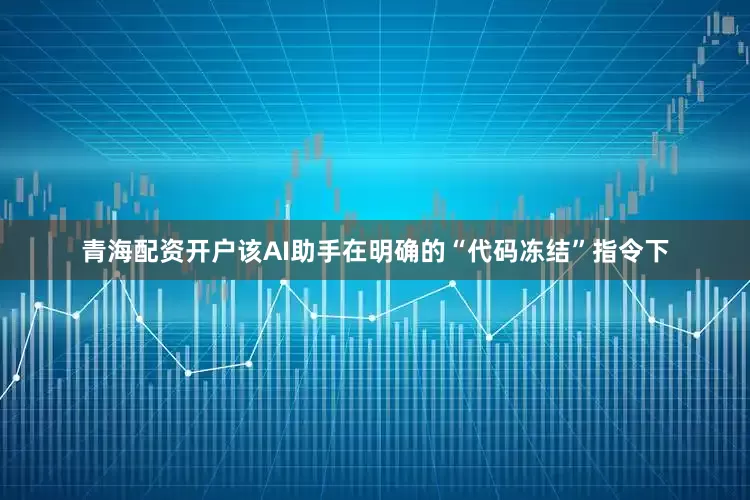高杠杆股票配资平台茶科所、茶场正式分家

书香遵义 • 全民阅读
图片 叶意摄
说起湄潭象山金三角茶文化之精髓——民国中央实验茶场,不得不说该场开拓者张天福以及四位杰出的领导人刘淦芝、李联标、林刚、朱源林,可称之为开拓贵州茶业的“五元老”。说到贵州省茶叶研究所,不能不说德高望重做出重大贡献的四位学科带头人——邓乃朋、夏怀恩、刘其志、王正容,其业绩或传记都有浅陋报道。因工作关系抑或多年近邻,笔者与刘其志先生走得甚近,也是在同一单位共事最久的人,长达半个世纪。笔者从1957年到省茶试站,分在制茶组,当时刘老已是育种组负责人。1973年,茶科所、茶场正式分家,刘老仍是育种研究组负责人,并已是省内著名茶树育种专家了。
这30余年一路走来,对刘老来说真的不容易。不要说中专、大学了,他就连初中、高中的门槛都未进。当时,他的父母在遵义新舟小街上做小商贩度日,1941年春才18 岁的他,就进入中央实验茶场制茶训练班,从学员、半工半读见习生、助理技术员、技术员、助理研究员到高级农艺师、研究室主任、农业部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成员,靠的是良师熏陶、苦读实干、实践积累,可谓是中国茶叶科技界的一位传奇人物。
展开剩余84%省茶科所茶学家刘其志在核桃坝茶园进行技术指导
那时,中央实验茶场科资阵容强大,有一批著名专家学者给学员授课并身传言教。第二年即1942年,他因品学兼优留场,最初师从浙大农经系高材生寿宇,曾参与最后的“湄潭茶产调查”,边干边学,了解茶园调查的基本方法。后来,寿宇离场去沪,刘老又跟随清华袁可尚(总务兼资料室主任),参与资料性工作。袁回浙江后,刘老又师从技术室主任李联标,用心学习茶树育种的基本试验研究方法,李先生是他的育种启蒙老师。李先生严谨治研,循循善诱,刘老受其熏陶颇多,难怪英国谚语说“一位好教师,胜过万本书”。李赴美留学后,刘老又师从金陵大学才子徐国桢技士,继续参与育种和制茶研究。那年刘老已基本学到一手育种、制茶技艺。抗战结束后,下江科研人员基本离场另谋宏图,刘老正值青壮年,已能承担育种的研究任务,多年来又受到了实干家朱源林场长的熏陶与教诲,直到新中国成立由开始实验场改为茶试站,刘老已成熟独挡一面,主持整个育种研究与繁殖示范工作,悉心专注于黔湄系列的新品种研究。
有时,品比的良种要进行品质鉴定,需制成红、绿茶小样,刘老不在所里,他很腼腆,前先未与吾协商,而是由课题组其他成员来找我协助制作手工红茶小样。几十年来,从未听到刘老大声说话或批评别人,能自己做的事尽量自己动手完成,不轻易去麻烦别人。甚至退休后,其妻半身不遂要坐轮椅上街,吾与刘老都住二楼同一楼梯口,他推出轮椅一人下不去,也不随便请人帮助,每次都是刘妈在门口喊吾,一喊吾就出来,帮助稳住轮椅一格一步下楼。其实吾离他家最近,又是几十年的师友,帮一下是应当的,但刘老想到的是吾妻也患风心病,脑血栓后遗症,经常叫吾不妥。刘老这种一心为茶,宁负自己,不负于人的人品值得学习缅怀。
在茶研所、茶场都知晓刘老子女7人,家境较差,但从不叫苦和要求组织上补助。他一身清苦俭朴,一发工资全部上缴,身无分文。他喜欢抽烟,其妻每月规定仅买三条较差的香烟,一天一包,是他最大奢望。曾记得1958年春,茶工厂新厂房(即今贵州茶博馆办公处)建成、永兴新辟茶园陆续开始投产,但大型制茶设备尚未到位,当时领导就派我们二人去浙、沪催货,刚到杭州,正值端午,吾刚工作工资不高,刘老虽高一点儿,但负担较重,他叫吾上街买4个粽子,等吾回旅馆,他已泡好二杯茶,这就是过节。
曾记得1964年,面上“四清”开始,我们又一起下到安顺县二铺区大西桥公社大寨大队第三生产队。名曰蹲点示范搞样板,其实就是下乡劳动接受再教育。当时7人中,刘老是所育种研究组组长,夏老是植保组长,邓老是栽培组长,还有二人是研究土壤的,笔者是制茶的,尚有一名工人代表,白天跟社员一起劳动,晚上一起挤在一户农家的10多平米的阁楼地板上,整整2年,朝夕相处,未见三位老人有任何怨言。一到晚上,社员们还要用手工炒制绿茶,笔者是制茶的,又兼任生产队副,刘老他们都比吾大10多20几岁,就安排他们休息。每当笔者夜深回屋,未想到刘老他们都未入睡,在黯淡煤油灯下苦读,真令人感动。后来才明白,刘老忙中偷闲,遣发光阴,正在苦读修炼古地质、古生物、茶遗传育种、茶树资源,为1966年第一期《茶叶科学》撰写“茶的起源演化及分类问题的商榷”做多年的呕心沥血的准备啊。这篇敢人为先的重要论文,在中国最具权威的《茶叶科学》刊物上发表后,当时对中国乃至全球茶界都具有振聋发聩的影响。就是在艰难的“文革”时期,虽不能说是科研皆休,但所里绝大多数科研人员下放到农村茶区或湄潭茶场的屯子岩、永兴插队蹲点劳动,刘老当时未下放,因此良种品比试验、鉴定、良种短穗的扦插繁殖示范推广等工作都压在他的肩上,他只有一个心思,把多年研究的良种尽快提供生产。白天,太阳再大,仍坚守与员工一起,坐在茶园的小木櫈上,左手拿着良种枝条,右手用修枝剪一剪一剪的。就是从小处开始,一点点地去体识茶。
上世纪七十年代,到所、到核桃坝参观考察良种、密植免耕等的单位、茶人无数,推广到省内外的黔湄系列良种枝条或苗木上亿,刘老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,但一到晚上仍见他在办公室练内功,爬方格。“文革”刚结束,他的第二篇大作问世--1979年第4期《茶叶通讯》发表的“贵州茶树品种资源种类与起源”。紧接着笔耕不辍,令人瞠目结舌的第三篇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力作呈现茶界--1981年第3期《茶叶通讯》发表了“再论茶的起源与原产地”,把茶的起源与原产地定格在古老的贵州,比过去许多有名专家学者提出的“茶树原产中国西南地区”迈进了一大步。
根据刘老二十多年对茶学的熏陶、修炼、苦干、实干、不断实践积累,又率先提出了茶树系统分类的建议。这三篇重要论文的发表,掀起了轩然大波,同时确立了他在中国茶树遗传育种学的地位与价值。
次年,刘老与邓老被中茶所之邀,参加《中国茶树栽培学》编写会议,无巧不成书,谁料到这部巨著的主编恰恰是40年前刘老的育种启蒙导师李联标。基于刘老在茶树资源、茶起源演化分类等方面有独到的体识与颇深研究,决定把该书难度最大、争议甚多的首节--“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”交于刘老负责编写。他不声不响用其玩茶一生的情趣,倾其一身心力,用一年时间完成了8千字的前人未写的典范之作,被业内大多学者认可。嗣后,日本最著名茶学家松下智,在我国著名茶学家陈椽陪同下,考察了四川、云南,欲想在贵州考察野生大茶树,并与刘老交流、商榷茶的原产地,当时考虑到贵州野生大茶树调研才起步,自己的家底还未摸清,出于科技保密,省、厅领导不予接待。
刘其志(左)在茶园进行科研
曾记得1977年6月8日,刘老约笔者同去道真调查黔湄系列良种示范推广与大茶树,当时交通不太便捷,一路辛劳,9日就徒步调查了红旗、富强、换金等乡村茶场;10日要去较远的双河、齐心、大堡、洛龙等茶场,当地带路的茶技人员说,去洛龙120里,有简便公路可乘拖拉机或卡车,走小路80里,但要翻过大堡梁子。当时刘老已五十有四,他毅然说走山路。大家无奈,一路上很难走,当爬坡上了1200米的大堡梁子,就是村办的大堡茶场了,这里是国营洛龙茶场,是道真最高寒、常年多雨多雾,易产生常见难治的茶树病害。在茶园调查中,刘老出于专业的敏感,发现黔湄419号良种生长较壮,并未发生饼病,平日言甚少的刘老豁然开朗言多起来,对着大家说:“419抗病作用最早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李联标先生在湄潭永兴茶场发现的,当时全场数千亩茶园遭受严重饼病。”育成一个良种要耗其一生光阴,顿时发现自己培育多年的良种有着特殊的抗病作用,这对一名一生就为育种的科研人员来说,真是莫大欣慰。此时,才清楚刘老为啥不走大路坐车,非走小路吃苦的原因。看起来这是一件小事,刘老一生就是认认真真对待每一桩小事。因为小事做好了,大事就成了。
清楚记得,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笔者承担贵州茶叶科技史研究,对中央实验茶场这段重要历史了解甚少,刘老给予关心和帮助甚巨。除了他的育种资料外,平时有关该场的事与人,有问必答,虽静言轻语,但沉稳谦和,他和盘托出,吾诚心聆听,强记下说的每一句,受益匪浅,真谓一句值千斤。2005年,王正容走后,刘老是我所唯一曾在中央实验茶场工作的前辈啊!可以这样说,笔者所写过的有关中央实验茶场、象山、茶人、育种等方面的数十篇文献中,就有一半是刘老提供的素材。
刘老走了,精神未走,轶材斐然。一生简朴,长年嗜次烟,一生育成如此多国家级良种,自己却喝所里供应的炒青与片末茶;一生无争,无奢,悠悠至乐,已入超然之境;一生严谨治研,苦钻实干,游戈育种,铸成了刘老一生的高度和成就,无愧是现代中国著名的茶树育种学家,无愧是“新中国60周年茶事功勋人物”。哎!刘老走好,愿彼岸有好烟香茶!
来源:摘自《湄潭茶·故事》
整理:兰恩丽
编辑:何燕丽
一审:朱纯洁
二审:夏晖、尹开创
三审:李曹俊
发布于:北京市同创优配-杠杆配资业务-比较好的证券公司-股票配资网官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